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要想让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
还需要做多项工作
“铁腕治检”再受关注。
7月29日,山西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该委员会主任由省检察院“一把手”杨景海担任,除内部委员外,还有六位特邀委员,由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担任。
除了山西,今年以来,湖北、北京、青海、浙江等多个省份陆续成立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而在2024年12月30日,最高检也成立了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主任是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
最高检民事行政监督检察咨询专家、安徽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专家委员库成员安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察官是专业性极高的职业,对于检察官履职行为的判断,理应交由更专业机构负责,通过惩戒委员会作出专业性判断并进行惩处,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不过,也有多位受访者表示,要想让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还需要做多项工作。
 2024年12月30日,最高检成立了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图/视觉中国
2024年12月30日,最高检成立了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图/视觉中国为什么要成立?
一起手机盗窃案,移送到检察机关时,犯罪嫌疑人突然翻供。这起案件有作案工具等物证,以前,承办检察官刘莉会给出批准逮捕意见,至于捕与不捕,由检察长审核决定。如今,在短短7天期限内,她先是将笔录送到技术部门鉴定,又对犯罪嫌疑人测谎,结论出来后,再对其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带来的变化,也是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成立背景。
2015年9月,最高检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时任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检察长潘祖全提到,在以往的办案模式下,“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弊端凸显,一旦发生错案、不诉、撤回起诉等案件质量问题,有关人员共同承担责任,导致权责不分明的矛盾。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加良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年来,我国强调对检察官和法官的依法履职进行保障,但对他们违法履职的惩戒有所缺位,因此有了这项改革。
司法责任制改革推动之后,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明确办案人员对其承办的案件质量要终身负责,即便办案人员已经调离或退休,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之后,检察官法修订,提出最高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这些年来,多个省份陆续成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2016年,重庆市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2018年4月,四川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2023年12月,福建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
惩戒委员会究竟如何履职?最高检检务督察局局长、巡视办主任郭兴旺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一个例子。吉林省检察院在调查一起下级院撤回起诉抢劫案相关人员司法责任时,发现当事检察人员以年龄大、记不清为由对调查避而不答,调查组在做好其心理疏导的同时,加强对相关人证、书证的收集,以扎实的证据证实其作为分管院领导没有依法履职,对于造成案件错捕、错诉以及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严重后果应当承担司法责任,受到政务记大过处分。
事实上,2022年3月,最高检印发了《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也对惩戒委员会这一较新的事物进行具体规定。
上述文件提出,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从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职业操守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等专业人员中选任。其中,委员总人数应为单数,检察官委员不少于半数。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经过审议,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情节和相关规定,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
另外,2024年,最高检新修订的《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检察院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经调查认为检察官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报检察长批准后,提请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针对近年来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再次遇热”,特别是今年以来,多个省份纷纷成立该委员会的原因,刘加良解释称,当前,国家要把司法责任制改革纵深推进,所以大力推动惩戒委员会的成立,并希望其可以产生实质效果。“成立该机构后,律师、当事人或当事人亲属一旦发现办案人员存在违规行为,就多了一个举报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检察系统之外,今年1月,最高法也成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主任是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多个省份也陆续成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
 2025年2月20日,湖北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图/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2025年2月20日,湖北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图/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因何成为“沉睡机构”?
尽管惩戒委员会并非新生事物,但公开的案例并不多见。
2020年,河南省检察院收到反映洛阳市某基层院在办理张某某寻衅滋事一案中存在违规违法办案问题的举报信。经初查,发现该案承办检察官李某某涉嫌违反检察职责,遂按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之后,省、市两级检察院共同组建专业化团队,对李某某开展司法责任调查,并组织一线检察官和刑事检察业务专家对调查结论反复论证、严格把关。
经查,李某某为争取办案时间,错误理解和适用退回补充侦查的有关法律规定,在原案指定管辖前已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下,第三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的规定,造成办案期限超期,并引发信访问题。
李某某在后期已经意识到此问题的情况下,为掩盖自身错误,在该院检委会研究此案时未如实汇报有关情况,导致该问题未被及时发现和处理。
经审议,17名惩戒委员会委员中有15人认为“李某某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司法责任”。最终,惩戒委员会根据审查意见和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李某某警告处分。
这起惩戒案例作为“全国首起检察官惩戒案件”,入选了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改革典型案例。这也意味着,我国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5年后,才出现首起检察官惩戒案件。此后,我国虽有多个省份成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但鲜有相关通报案例,在部分学者口中,该委员会甚至被称为“沉睡的机构”。
华东地区一位县级检察院检察官孙虹(化名)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地方很少有检察官被惩戒的案例,“如果不是发生特别过分的情形,办案人员通常不会受到这种惩戒”。
张庆军是京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刑委会副主任,任检察官时曾当选过“省级优秀公诉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从多个省份惩戒委员会的运行情况看,此前惩戒制度运行得并不顺利,没有落到实处。
多位受访者称,该委员会“沉睡”的原因,与多种因素有关。
在张庆军看来,惩戒委员会本质上是一种上级监督机制,但目前,部分规定不够细化和明确。孙虹则进一步提到,因为检察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下,如何判断检察官是行使自由裁量权,还是存在过错甚至“重大过失”?目前,认定标准不一。“有的案件会受到多种因素干涉,甚至干涉压力在检察系统之外,这就导致最后责任认定困难,影响惩戒效率和准确性。”孙虹举例称。
还有受访者提出,惩戒委员会和纪委监委相关职能、检察部门自身的检察侦查职能有所重合的问题。
河南省某市检察院公诉处一位原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检察机关本身就设有纪检监察组,与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大同小异。安超也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和监察机关同时拥有对检察官违反职责行为的管辖权,当二者冲突时,“很可能会导致检察官惩戒制度被架空,惩戒委员会空转”。
刘加良则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认为,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和纪委监委的工作界限较为清晰。惩戒委员会侧重“对案不对人”,在确定因人为因素出现冤假错案时才会追责到人;而纪委监委侧重“对人不对案”,其重点在于调查处理办案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惩戒委员会一旦发现后者的线索,也应将其移交纪委监委。
至于检察部门自身的检察侦查职能,刘加良表示,其面向刑事侦查人员、刑罚执行人员、检察官、法官等所有司法工作人员,针对的是这类人员涉嫌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等14个特定罪名时,对他们进行立案侦查。而惩戒委员会则在检察官和法官出现违法履职时进行惩戒。
如何保障“实质化运行”?
多位受访者表示,要想让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还需要做多项工作。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审查意见的约束力不明。安超表示,当前,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查案件,是采取听证会还是书面审查的方式,相关法律还未予以明确。如山东提出“委员会审议检察官惩戒事项,原则上实行书面审议制度”,而山西规定“惩戒委员会审议检察官错案责任案件,应当进行听证”。此外,还有云南、湖南、黑龙江等省份均表示,应以听证的方式进行审议。
多位受访者都表示,采取听证的审查方式得出的结果更为客观,但比起书面审查往往要付出更多成本,耗费时间也更长。
此外,检察院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是否必须完全采纳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审查意见的采纳范围又是否可以自行作出选择等,安超认为,在今后的规定中也应予以明确。
关于惩戒制度和监察制度的衔接问题,安超建议,未来应该探讨建立衔接机制,以便于解决当被调查的行为具有双重性(即属于监察制度与惩戒制度管辖重叠)时,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多位受访者还提到,在强调惩戒的同时,有必要设置容错机制。张庆军提出,因司法解释修改、证据链发生变化、国家政策调整等,造成办案质量不高等情形,不应当追究检察官、法官的责任。
郭兴旺列举了这样一个容错免责案例: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在调查一起再审改判无罪故意伤害案当事检察人员司法责任时发现,原审被告人改判无罪主要在于,过去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总体仍较为保守,并且再审期间出现新的证据,而当事检察人员办案时已经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而认定当事检察人员不需要承担司法责任。
另外,需要考虑具体办案中,公检法之外力量介入的问题。张庆军说,从近年来纠正的一些冤假错案看,这一问题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纠正之后,还要再对办案人员追责,确实很难让办案人员接受。但也需要考虑:问题案件已经酿成,这样的理由真的能成为检察官或法官免责的依据吗?”
他建议,今后可以探索建立一套独立于检法机关的第三方机构,科学评判与奖惩检察官、法官的办案行为,该机构可以隶属于人大常委会,便于更公正合理地评价他们的履职。
有受访者提到,员额制的退出或可作为惩戒委员会对相关办案人员的惩戒方式。刘加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员额法官(检察官)的退出机制还不够完备的现实,今后,惩戒委员会可以根据办案人员涉及问题的性质及后果,决定是否做出让其退出员额的审查意见。“这种方式既能起到震慑作用,还有助于打通员额制的出口通道。”
记者:周群峰
责任编辑:刘光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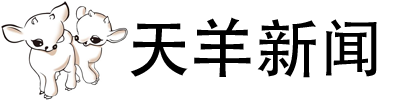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